为什么一些精神疾病,如焦虑和抑郁,呈上升趋势?像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这样的疾病是否会带来进化优势?为婴儿筛查未来的脑部疾病是否合乎道德?
在这一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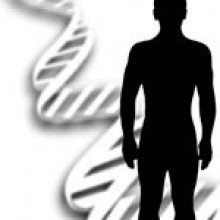
有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吗?
剑桥大学的Barbara Sahakian教授,卡迪夫大学的Michael Owen教授
精神疾病有很大的污名。然而,四分之一的人在一生中会经历精神疾病。在英国的任何时候,六分之一的人都会有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生活抑郁和焦虑。
精神疾病甚至影响到更多的人,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更多, 癌症。因此,科学家、临床医生和政府都在寻找生物标记,包括基因测试,这些测试可以帮助诊断有精神疾病风险的人,以便在他们完全出现症状之前发现他们。
癌症。因此,科学家、临床医生和政府都在寻找生物标记,包括基因测试,这些测试可以帮助诊断有精神疾病风险的人,以便在他们完全出现症状之前发现他们。
为了了解更多,我采访了卡迪夫大学的迈克·欧文教授和剑桥大学的芭芭拉·萨哈吉安教授。我首先问迈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精神疾病?基因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迈克:有很多不同的精神疾病,从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智力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一直到轻微的抑郁症和焦虑症,这些通常由全科医生或临床心理学家治疗。
至于基因的作用,实际上,基因在几乎所有事情中都起着作用,也许程度不同。但我们的很多行为都受到基因的影响。当你想到我们是这样一个社会物种,自然选择很可能对影响行为的遗传变异起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
确实,更严重的疾病似乎有更强的遗传基础。遗传率较高。作为一种经验法则,更严重的疾病,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影响的相对贡献可能比较轻的疾病更大。
汉娜:那么,如果一个婴儿出生,他们会患上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吗?他们天生就有这种疾病的基因吗?
迈克:嗯,是的。人们遗传的是一组基因,这些基因使他们或多或少容易患上这种疾病。这些疾病都没有基因。基因会受到影响,蛋白质会影响神经细胞,影响回路,等等等等。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会打一副牌这让我们或多或少有可能患上特定的精神疾病,这取决于整个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情况。
汉娜-芭芭拉……
芭芭拉:举个迈克刚才说的例子,我们有一篇论文 马修·欧文斯和伊恩·古代尔研究了那些经历过逆境的孩子主要是心理上的逆境,看着他们的父母在他们面前打架,争吵,对彼此大喊大叫,打对方。然后我们跟踪这些孩子到青春期,我们发现他们有这种消极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认知上衡量。但正是这种早期的逆境加上这种思维方式以及s等位基因作为血清素转运基因这意味着在青春期,不幸的是,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组合就像迈克说的环境因素和基因因素的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马修·欧文斯和伊恩·古代尔研究了那些经历过逆境的孩子主要是心理上的逆境,看着他们的父母在他们面前打架,争吵,对彼此大喊大叫,打对方。然后我们跟踪这些孩子到青春期,我们发现他们有这种消极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认知上衡量。但正是这种早期的逆境加上这种思维方式以及s等位基因作为血清素转运基因这意味着在青春期,不幸的是,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组合就像迈克说的环境因素和基因因素的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汉娜-这似乎适用于所有的精神疾病。你提到了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还有抑郁症和焦虑症。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会有早期的生物标记来提示吗?比如说,你可能会去看医生,在你刚出生的时候,在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采血,分析你的基因,然后你就会知道你是否有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如果在你的一生中,在你大脑的其他部分的发育过程中,有一些事情是你应该注意的,你应该保护自己。你认为这种情况将来会发生吗?
迈克:嗯,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尽管我研究遗传学很长时间了,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确定答案是什么。我认为大脑可能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系统。
我认为人们可能有点天真地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预测像精神疾病这样非常复杂的疾病是非常容易的。但我确实认为,我们会有一些牵引力,能够——不同易感人群,总体上会有粗略的、现成的估计。现在,例外的是,有一些相当罕见的基因突变会导致很高的精神疾病风险。今天的许多药物,实际上不仅会给精神分裂症带来风险,还会给自闭症,智力障碍和多动症带来风险。在那里,风险是相当高的携带这些突变的人已经与服务机构取得了联系,但他们通常是遗传服务机构,可能是儿科神经学家。我认为临床小组还没有弄清楚如何应对精神疾病风险的增加。这些都是例外。所以,像这样的突变导致了少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当然,当我们开始用我们所拥有的新技术做更多的测序时,当我们很快就能对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时,也许更多的这些罕见的东西会出现。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认为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更像是预测天气。
芭芭拉:我也认为,显然有很多神经伦理问题与这类领域有关。因此,我们必须非常关注这些问题,并随着事情的发展而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心理健康障碍已经有了太多的污名,我们显然必须努力解决,因为我认为它不应该存在,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坦率地对待它们,我认为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精神健康障碍方面需要做出更大的改变。
就像迈克说的,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如此明确,其他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以及你能做的积极的促进因素是什么,以确保一个人有良好的生活质量,而他们实际上不会患上这些疾病。所以也许,我们应该做的是,与年幼的孩子一起工作,然后在学校里与他们一起工作,帮助他们制定计划,培养他们的适应力和良好的大脑健康,这样他们就不会屈服于这些事情。然后,尽早发现它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者完全阻止它的发生,或者早期发现并有效治疗,这样它就不会变成慢性和终身的。
汉娜-请记住,在这种生物基因测试可能在未来可用之前,四分之一的人会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候经历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能做什么?此刻我能做些什么来保护我的心理健康?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我5、6岁的侄子保护他和我母亲未来的心理健康?我们都能做些什么呢?
芭芭拉:嗯,我非常赞成“要么使用,要么失去”的想法,我认为你必须这样做 保持思维活跃。我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是终身学习。所以,学习新事物总是好的。我们知道新的学习产生神经新生,海马体产生新的细胞。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其他事情,比如锻炼。我们知道这也与海马体中的神经发生有关。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我们的大脑长时间更好地运作。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对心理健康有益的事情。所以,联系和活在当下的想法,这种正念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基于证据的幸福方法。 We devised about 5 of these for the ment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project and by the foresight. That was one of them and another one had to do with giving because actually, when they've looked at people giving to their favourite charities and they've had them in scanners, the reward system in the brain is actually activated. So, the individual finds that very positive in rewarding as well as obviously, the person that they're giving to. So, giving is good yourself as well as for the other person. So that's another thing that we can do. The other thing is support systems - social support systems that we need to be more attentive to develop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and the community. That is also been shown to be beneficial for mental well-being.
保持思维活跃。我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是终身学习。所以,学习新事物总是好的。我们知道新的学习产生神经新生,海马体产生新的细胞。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其他事情,比如锻炼。我们知道这也与海马体中的神经发生有关。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我们的大脑长时间更好地运作。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对心理健康有益的事情。所以,联系和活在当下的想法,这种正念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基于证据的幸福方法。 We devised about 5 of these for the ment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project and by the foresight. That was one of them and another one had to do with giving because actually, when they've looked at people giving to their favourite charities and they've had them in scanners, the reward system in the brain is actually activated. So, the individual finds that very positive in rewarding as well as obviously, the person that they're giving to. So, giving is good yourself as well as for the other person. So that's another thing that we can do. The other thing is support systems - social support systems that we need to be more attentive to develop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and the community. That is also been shown to be beneficial for mental well-being.
Hannah -非常感谢你,Barbara和Mike抽出时间与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我有一些听众的问题,如果你能花点时间回答就太好了。
因此,大卫·贝利和史蒂文·奎尔一直在联系,他们问:“为什么心理健康问题如此普遍?它们现在比一百年前或一千年前更普遍吗?”
芭芭拉:不幸的是,我不能回答是一百年前还是一千年前,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形式的精神疾病正在增加,这些疾病往往与压力有关。全球化、与他人竞争工作等似乎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失业让人压力很大,债务让人压力很大。因此,在这个经济紧缩的时代,压力的程度往往会提高,因此,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发展更多的焦虑和抑郁。
迈克:是的,当然。我认为我们现有的证据并不是很久以前的证据表明像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这样严重的疾病可能是一样的。就严重的疾病而言,自闭症是个例外。但问题是,这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还是因为一些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更普遍的。对于这种在现代生活中特别容易引发精神疾病的想法,我没有一个特别科学的答案。我是说,我怀疑我们更注重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一种奢侈,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当奢侈的位置上,能够反思我们的感受和我们是怎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以前没有的。
芭芭拉:迈克说得很好,因为我们从质量护理委员会得知,治疗多动症的兴奋剂处方,如利他林,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在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例子是首先,这些疾病得到了更多的识别。例如,对于某人的祖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小时候患有多动症。因此,认知度要高得多。第二件事是,多年前,我们认为多动症在童年或青春期就结束了。现在,我们知道它会持续到成年期。
汉娜——同样的,苏珊一直在和我联系,她说:“有人告诉我,焦虑可能源于对压力情况的一种天生的‘逃跑或战斗’反应。这是真的吗?”所以,我们的恐惧和焦虑的感觉是我们进化出来的,它有助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
迈克:焦虑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适应性反应。它是“战斗或逃跑”过程的一部分,是一种表现。当它开始走出自己的盒子,出现在一个不合适或不合适的情况时,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这是一种,人们可以推测出其他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也是如此。悲伤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但当它从盒子里逃出来时,它就变得病态了,或者我们称之为病态。
汉娜:有时候,感到悲伤并对特定的情况做出反应是非常有用的,这可以帮助你确保你不会再遇到同样的情况,例如,你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苏珊还说,“有没有其他的行为,比如多动症,被认为与有助于我们祖先生存的特征有关?”
芭芭拉:多动症,实际上,我做过一个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行为的研究。当我让一些人填写量表的时候就像我让ADHD诊所的成年人填写的量表一样,他们的得分很高。所以关键是,如果你能引导人们的一些活动和做事情的热情,它实际上是相当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帮助我们利用时间有限的机会。所以,ADHD患者的一些特征或特征——如果引导得当——是非常有用的。
感谢剑桥大学的Barbara Sahakian教授和卡迪夫大学的Mike Owen教授。

大脑奖!
剑桥大学的特雷弗·罗宾斯教授
 剑桥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特雷弗·罗宾斯教授刚刚被宣布为格雷特·伦德贝克大脑奖的获奖者之一:100万欧元,以及对获奖的欧洲大脑研究人员的许多荣誉。
剑桥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特雷弗·罗宾斯教授刚刚被宣布为格雷特·伦德贝克大脑奖的获奖者之一:100万欧元,以及对获奖的欧洲大脑研究人员的许多荣誉。
我设法在他做剑桥神经科学讲座的间隙和他聊了一会儿。我首先问他在过去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是什么让他的大脑忙碌起来的.......
特雷弗-嗯,我一直在几个领域工作。我想,作为一个一般的主题,我一直在研究额叶和大脑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额叶调节着大脑的一些高级功能。它们控制我们的行为,帮助我们计划、做决定和影响判断,同时,对我们的行为施加控制或自我控制,阻止我们变得过于冲动。
汉娜——这些额叶位于我们前额的后面,与许多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额叶非常大。
Trevor:是的,我的意思是,有些人认为人类的大脑比老鼠的要大。
汉娜: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有什么主要发现?
特雷弗:嗯,一些主要的发现与大脑中的特定回路有关,这些回路存在于大鼠和小鼠等动物身上,也存在于人类身上。尽管它们在人类身上更为发达。我们还研究了大脑中的一些化学信使,它们是如何调节或影响这些回路的功能的,这些化学信使同样存在于老鼠和人类身上。这在治疗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治疗强迫症、成瘾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疾病的一些药物非常有效,但它们可以更有效。所以,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大脑如何调节这些行为,还有如何使它们变得更好,改善它们。
汉娜:所以,你的研究确实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与这些决策行为有关的大脑回路,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人实际上受到影响的冲动、有时强迫和成瘾行为的风险。同时,也帮助开发了治疗这些疾病的新方法。
特雷弗-没错。有趣的是,不久前我们发现老鼠喜欢 以可卡因为例,就像兴奋剂——可卡因、安非他命、甲基苯丙胺——往往是非常冲动的。他们的行为往往很冒险。我们把这个想法应用到兴奋剂滥用者身上,发现兴奋剂滥用者显然从定义上看,确实表现出冲动和危险的行为。但我们能发现的是,这些倾向可能在他们开始吸毒之前就存在了。因此,它们可能会使人倾向于吸毒,从而增加冲动,我们认为,从冲动行为到强迫行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这在大脑中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成瘾开始于基底前脑的一部分。这是前脑中被称为伏隔核的部分。这就是最初的药物记录的地方。但似乎他们应该长期服药,因为你接触的药物越来越多,它会占据大脑的其他部分,而这些部分与控制习惯和自动行为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自动行为导致了强迫性的药物寻求行为,你会在吸毒者或物质依赖者身上看到。
以可卡因为例,就像兴奋剂——可卡因、安非他命、甲基苯丙胺——往往是非常冲动的。他们的行为往往很冒险。我们把这个想法应用到兴奋剂滥用者身上,发现兴奋剂滥用者显然从定义上看,确实表现出冲动和危险的行为。但我们能发现的是,这些倾向可能在他们开始吸毒之前就存在了。因此,它们可能会使人倾向于吸毒,从而增加冲动,我们认为,从冲动行为到强迫行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这在大脑中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成瘾开始于基底前脑的一部分。这是前脑中被称为伏隔核的部分。这就是最初的药物记录的地方。但似乎他们应该长期服药,因为你接触的药物越来越多,它会占据大脑的其他部分,而这些部分与控制习惯和自动行为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自动行为导致了强迫性的药物寻求行为,你会在吸毒者或物质依赖者身上看到。
汉娜:通过观察自我服用可卡因的老鼠,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证据。
Trevor:有些想法当然是来源于那些动物模型。事实上,还有一些治疗这些倾向的方法。例如,这些高冲动的老鼠可以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来减少冲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以,这向我们表明,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治疗方法,可能对有成瘾风险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帮助他们控制自己、不沉迷于这些危险行为的方法。我们也明显受到我们在诊所看到的影响,这也有助于我们改进动物实验。
汉娜:特雷弗,快说一下,你对这一领域神经科学的未来研究有什么兴奋之处?
特雷弗:天平的一端是遗传学。例如,如果你有一只老鼠或一个人非常冲动,这种冲动的起源是什么?这是基于他们的经历,也许是他们年轻时的压力,或者是他们的基因构成,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结合?我认为它在未来会非常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对大脑成像的分辨率越来越高,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回路在哪里,哪里出了问题,这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因为成像技术越来越好,分辨率也越来越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回路中非常微小的变化,我们认为这在人类和其他动物身上是一样的。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前景。
汉娜-最后是特雷弗,你是2014年100万欧元大脑奖的获奖者之一。你打算怎么花这笔钱?你打算带你妻子芭芭拉去度假吗?
特雷弗-我们有几个想法。前几周我的电脑坏了,所以我想我可能会买一台新电脑——这是一回事。的确,跑车的想法非常诱人,但我认为,我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将其投入到研究中。
汉娜——这是剑桥大学的特雷弗·罗宾斯教授上周宣布他与他人共同获得2014年格蕾特·伦德贝克欧洲大脑奖时所说的话。

大脑了
凯特·麦卡利斯特,凯瑟琳·曼宁,马丁·奥尼尔博士
 在这个月的裸神经科学播客结束时,我将报道2014年剑桥神经科学会议,我想我应该看看其他一些研究,所以我采访了博士生凯特·麦卡利斯特、凯瑟琳·曼宁和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奥尼尔博士,听听他们的观点.....
在这个月的裸神经科学播客结束时,我将报道2014年剑桥神经科学会议,我想我应该看看其他一些研究,所以我采访了博士生凯特·麦卡利斯特、凯瑟琳·曼宁和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奥尼尔博士,听听他们的观点.....
首先,马丁…
Martin:我喜欢剑桥精神病学部门的Valerie Voon关于强迫症的研究。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收集信息的能力受损,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不确定的信息时做出决策时更加谨慎。这种谨慎或缺乏接受不确定信息的意愿可能是强迫症患者强迫性行为的基础。
这项研究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是关于基本的大脑机制和涉及风险决策的研究,这与强迫症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我的很多研究都是基础研究,所以我对大脑在正常的日常情况和风险中是如何运作的很感兴趣。当我提到风险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不确定性,这确实存在于我们经常做的大多数决定中。你知道,生活中很少有事情是绝对确定的。所以,我对基本机制很感兴趣,但正如这里的研究表明,它的基本方法也可以应用于临床疾病的研究,比如强迫症。但反过来,这些临床情况的发现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以及我们研究神经科学的基本方法。
汉娜-非常感谢,马丁。凯特·麦卡利斯特,你今天注意到什么了?
 我对Ian Goodyer教授的研究很感兴趣,他概述了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网络(简称NSPN)的建立这是伦敦和剑桥的合作。因此,NSPN成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青少年大脑数据数据库。所以,青少年的大脑在青春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其中之一是髓鞘形成。因此,改善脑细胞之间的连通性,同时,突触修剪,使神经元和神经元连接达到最佳状态。青少年时期实际上也是神经疾病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很多精神疾病都是从青春期开始的。同时,这也是第一次我们最容易受到冒险行为的影响。比如吸毒和滥用药物,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NSPN将研究2到2000名年龄在14到24岁之间的正常发展的人。 They're going to look at participants using cognitive tasks, behavioural insights, but also scanning. Something that's been quite a theme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 today that I've noticed actually has been the needs for collaborative large scale studies. As much as we have really amazing neuroscience research that's going at the moment, we still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hat much about the brain and I mean, we understand even a little bit the adolescent brain. So, we're really interested to follow the study and see what they find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bout that's really critical periods of neuromodulation.
我对Ian Goodyer教授的研究很感兴趣,他概述了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网络(简称NSPN)的建立这是伦敦和剑桥的合作。因此,NSPN成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青少年大脑数据数据库。所以,青少年的大脑在青春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其中之一是髓鞘形成。因此,改善脑细胞之间的连通性,同时,突触修剪,使神经元和神经元连接达到最佳状态。青少年时期实际上也是神经疾病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很多精神疾病都是从青春期开始的。同时,这也是第一次我们最容易受到冒险行为的影响。比如吸毒和滥用药物,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NSPN将研究2到2000名年龄在14到24岁之间的正常发展的人。 They're going to look at participants using cognitive tasks, behavioural insights, but also scanning. Something that's been quite a theme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 today that I've noticed actually has been the needs for collaborative large scale studies. As much as we have really amazing neuroscience research that's going at the moment, we still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hat much about the brain and I mean, we understand even a little bit the adolescent brain. So, we're really interested to follow the study and see what they find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bout that's really critical periods of neuromodulation.
汉娜-非常感谢。凯蒂·曼宁……
凯蒂:我认为詹姆斯·罗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一项研究非常有趣,他们大部分都在剑桥大学工作。他们研究了一种假设,即神经退行性疾病——也就是逐渐影响大脑的疾病——对大脑中具有更多功能连接的区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所以,这是在研究大脑的各个区域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而不是仅仅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
汉娜:所以,他们在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或亨廷顿氏症?
凯蒂:以前在阿尔茨海默氏症中也有研究,他们想看看这个想法是否也适用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观察了帕金森病、进行性核上性麻痹和皮质基底综合征。
汉娜-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凯蒂-他们用的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简称fMRI 通过观察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以及它们与其他区域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来建立一个网络的图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有一些区域有很多连接,来自或通过它们,这些区域被称为枢纽。因此,我们的假设是这些中枢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受到的影响特别大这些区域显示出最大的连通性丧失。
通过观察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以及它们与其他区域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来建立一个网络的图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有一些区域有很多连接,来自或通过它们,这些区域被称为枢纽。因此,我们的假设是这些中枢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受到的影响特别大这些区域显示出最大的连通性丧失。
汉娜:所以,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中枢,这些大脑中的网络,它几乎就像一个从大脑的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通信运输系统。这和英国米尔顿凯恩斯这样的城市相比怎么样?米尔顿凯恩斯有很多环形交叉路口,但有很多主要道路系统。以伦敦为例,那里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岔路,他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枢纽和连接节点是否与此相似?
凯蒂-是的,真的。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国王十字车站。
汉娜:所以,国王十字车站是英国伦敦的主要火车站之一?
凯蒂-是的。人们从全国各地前往其他地方。所以,它可能会直接穿过国王十字车站,然后穿过。所以,在路径上使用一种停顿。在这项研究中,他们有150名参与者,其中一些人患有三种疾病中的一种。然后还有一些无障碍的参与者。这些是对照组,他们是用来做比较的。他们还完成了一些测试他们认知能力的任务。对于研究中调查的所有三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人员确实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中枢的连通性有所减少。事实上,正如他们预测的那样,他们发现中枢连接性较弱也与一些认知任务的糟糕表现有关。 So, they suggested these hub regions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in many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and that their reduced connectivity that might then be really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these disorders, and in the future, be able to inform us in evaluating patients and finding information that might be useful for clinical treatment.
汉娜:所以,我想下一步是寻找方法来确保这些病人大脑中的国王十字火车站重新启动并开始工作。
凯蒂:是的,所以我想这种治疗的下一个观点是如何使用它来帮助患者群体。事实上,了解健康人群的大脑功能网络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患有某些疾病的人和患这些疾病的高风险人群的这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领域,目前还没有太多的研究。
汉娜:很不幸,我们这个月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剑桥神经科学为本期特别播客提供芭芭拉·萨哈吉安、迈克尔·欧文、特雷弗·罗宾斯、凯瑟琳·曼宁、凯特·麦卡利斯特和马丁·奥尼尔从剑桥神经科学研讨会发回的报道。








评论
添加注释